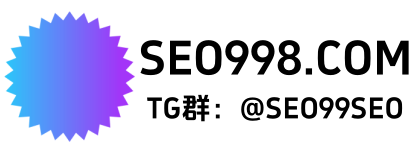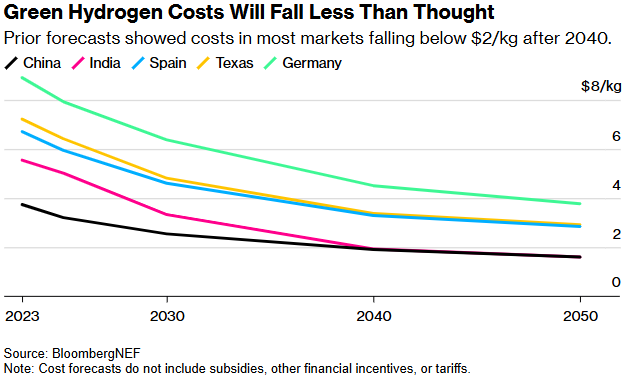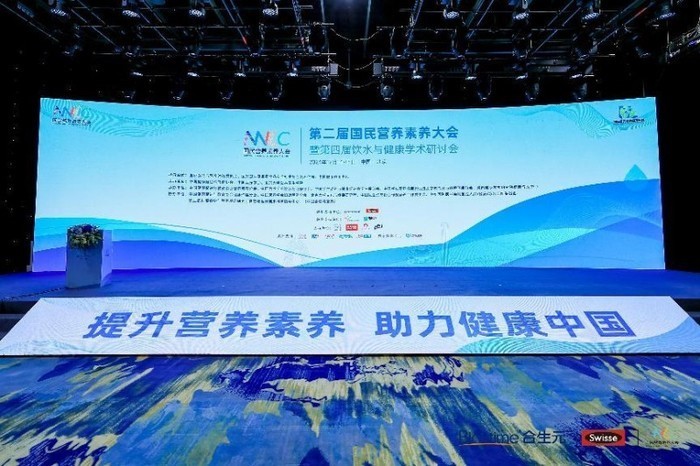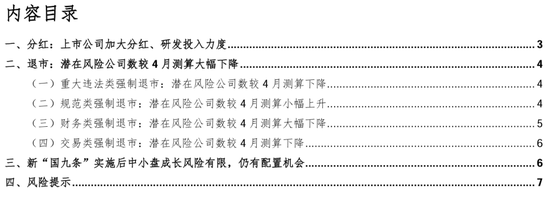金羊网娱乐:宅男影-张伟劼评《玻利瓦尔传》|是圣徒还是暴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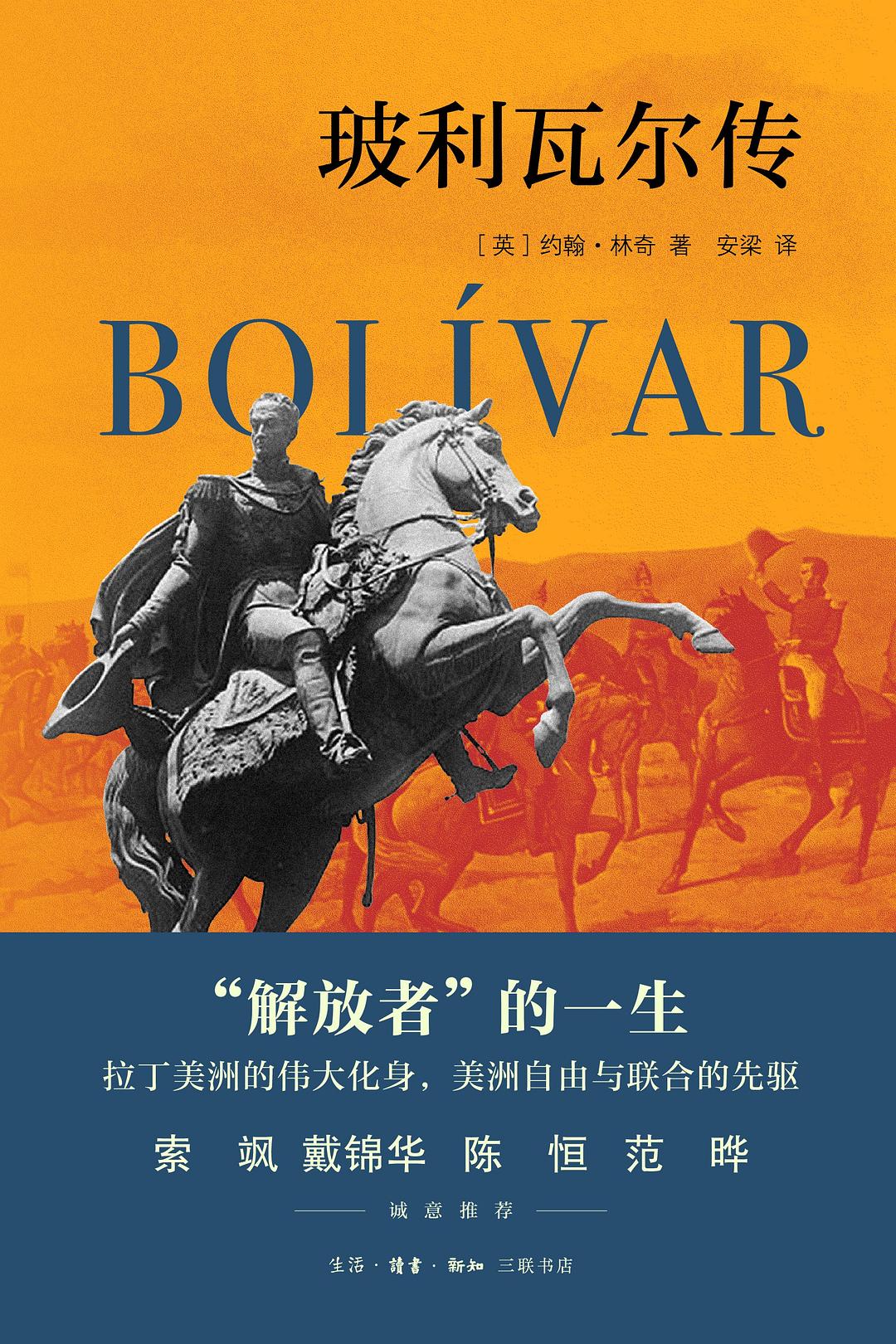
《玻利瓦尔传》,[英]约翰·林奇著,安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9月出版,465页,70.00元。
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曾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名句写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幽灵,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现代历史中游荡:一个是考迪罗崇拜的幽灵,一个是革命神话的幽灵。”考迪罗是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政治强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往往自诩为拯救民众于乱世、捍卫民族利益的救赎者,甚至还会宣称继承了西属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783-1830)的遗志,行独裁暴政之实,乃至于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曾讽刺道:“好吧,那么现在谁把我们从我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呢?”在克劳泽看来,十九世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那批思想家是对考迪罗和革命均持厌弃态度的,他们视此二者为阻碍文明进步的野蛮的化身,然而到了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在拉丁美洲人的观念中,此二者悄然经历了转变:“对考迪罗的批判,变成了对强人、对天选之英雄的崇拜;革命则享有盛名,成了民众眼里预示公正将至的新曙光。”考迪罗和革命者看似是对立的,前者不遗余力地防备、追捕后者,后者不遗余力地反抗、颠覆前者,但二者往往在事实上是一体的——现在的考迪罗是过去的革命者,现在的革命者一旦成功夺权就将成为新的考迪罗。就这样,这片土地在专制暴政和内战乱局间经历无止尽的循环。或许,这就是困扰着一代又一代“解放者”的拉丁美洲政治的迷宫吧。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和共识,拉丁美洲国家是走不出这座迷宫的。在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中,人们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过去,投向拉丁美洲在血与火中争取独立之时的迷宫一般的乱局,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于是,玻利瓦尔的行动和思想一次次地被检视,他的形象不断地得到新的诠释,关于他的争论远未终结。这位早已成为青铜塑像、甚至连名字都被固定在国名之中的历史人物,究竟算是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解放事业的圣徒,还是一个贪恋权力的暴君?或者两者皆是?
英国学者约翰·林奇的《玻利瓦尔传》展示了这位美洲解放者在他的宏伟事业中面临的重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为他正名:玻利瓦尔与后世的那些打着他的旗号倒行逆施的考迪罗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与平等是他始终坚持的信条,他一直尊崇来自人民主权的法律,并没有滥用手中的绝对权力;他也并不像一些文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时时展露出实用主义的倾向,懂得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理性的决策,然而,这在独立革命成功后的时代势必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诉求,最后他只能黯然离场,留下一个远去的孤独背影。这孤独的背影,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如幽灵般的“迷宫中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声明:“我已经不存在了。”或是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述,经历了幻灭的玻利瓦尔皮肤暗黄,双目无光,躺在一艘小船肮脏的帐篷里,顺着玛格达莱纳河而下驶向大海,驶向死亡,口中喃喃道:“我再也不行了。”
在《玻利瓦尔传》里,没有如此生动的画面,作者关于玻利瓦尔的一切言行思想均有据可循。“解放者”顺应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摆脱宗主国束缚和压迫的强烈需求,舍弃个人产业,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成长为独立革命的领袖,南征北战,屡败屡战,靠着坚强的意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的确符合一个圣徒、殉道者的设定。但玻利瓦尔绝不是盲目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势必会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他并没有将那些外国思想视为神圣不可变通的原则,并未照搬法国或美国的革命模式。约翰·林奇强调,玻利瓦尔是富有独创性的,尽管涉猎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他“遵循的不是西方世界的模板,而是他所属的美洲的需求”;尽管他熟读欧洲古代史,他并没有幻想着复兴古老的制度,而是认识到,“源自雅典、斯巴达与罗马的各类思想理念纷繁混杂,其结果是制造了偶像,而没有诞生法律,因此不适宜仿效,以建构现代国家”。自由也好,平等也好,在他看来都不是纯粹绝对的概念,而应在落地美洲时遵从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这就意味着,要对自由加以限制,以防它演变为无政府主义或暴政这两个极端状况;要确保平等不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而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惠及美洲社会肤色各异的所有人。“他领悟到,政治解决方案与政府模式,必须与美洲环境相适应,满足美洲需求。”这种思想在古巴诗人、革命者何塞·马蒂——又一位解放者——1891年写就的名文《我们的美洲》中发出了回音。马蒂写道:“在美洲,一个称职的执政者无需熟知德国人或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应当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知道如何通过源自本国的方法和习俗来引导全体民众,以达到理想的境界。”马蒂在文中断言:“汉密尔顿的法令阻止不了洛斯亚诺斯人的烈马。”意思是说,外国的政法制度无论有多么完美、多么负有盛名,都不适用于诞生自西班牙语美洲广阔土地的国民性。
那么玻利瓦尔眼中的“美洲需求”是什么呢?约翰·林奇断言,在他的时代,美洲最大的需求之一,就是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秩序逐渐解体的过程中,各种势力浮出水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利益、目的,与其他的势力保持或对抗或合作的动态关系。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各路军阀混战,这是在世界各地的各个不同时代都一再出现的局面。美洲军阀混战的乱局,应当说跟殖民地长期维持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深层的联系。西班牙人在美洲留下的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制,每一个种植园或是大庄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园主在自己的领地上统率着一众奴隶,其利益的重心在海外市场而非本地市场,这些封建领主在百年孤独中展开百年纷争。另一方面,从“独立”(independencia)一词的字面上看,独立意味着摆脱依附地位,意味着不再从属于任何人、任何势力,那么在美洲土生白人争取摆脱西班牙束缚的同时,美洲种植园里的奴隶也在争取摆脱白人主子的束缚。《玻利瓦尔传》提到,独立斗争催生了黑人奴隶的种族意识,黑人士兵可以为任何一方作战,带有很强的投机心理,并且总是专门针对敌方部队的白人大开杀戒,而西班牙人也懂得利用美洲居民的内部矛盾,说服黑人加入保皇党的队伍,与独立武装相对抗。独立武装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各路军事头目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地盘的利益。在故土委内瑞拉领导解放斗争的玻利瓦尔,面对的是一个野蛮的丛林世界,在这里武力比公理更管用。在这场大混战中,唯有比敌人更狠、更野蛮,才能确保军事斗争的胜利,在报复敌人的残忍行径时唯有以牙还牙、表现得比敌人更残忍,才能确保自己一众手下们的忠心拥戴。这就是作者所言的“灭绝之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其说这是一场美洲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内战,因为在战场上展开厮杀的主要还是美洲人。这种血腥内战,不幸成了拉丁美洲历史的一个传统,有时候表现为独立后新兴共和国之间的战争,有时候表现为一国之内的长期冲突,哥伦比亚就深受其害。《百年孤独》的第一句就揭示出这仿佛被诅咒的命运:“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将敌方俘虏枪决了事,是内战中的常态。这意味着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灭绝之战中都杀红了眼,没有谈判的余地,没有和解的可能,不能形成共识、坐在一起在法的框架下商量出个所以然来,非要取对方性命不可。在内战与暴政的轮回中,最苦的当然还是老百姓。
《玻利瓦尔传》提到,在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失败后,玻利瓦尔在卡塔赫纳宣称:“是我们的不团结,而非西班牙人的武器,让我们重新沦为奴隶。”玻利瓦尔由此认定,美国的联邦制国家、代议制政府与委内瑞拉的利益不符,唯有统一与集权才能确保胜利。在他眼里,联邦制“不过是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可能适合于一直浸淫于自由风气和开明政治环境的北美人,而要放在西班牙语美洲,则会导致政府的孱弱与分裂,他甚至断言,“南美洲与其采用美国的政府形式,还不如遵奉《古兰经》,尽管前者是世间最好的政府形式”。曾与玻利瓦尔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论证过,北美的联邦制不适用于南美。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联邦制固然是促进人类繁荣与自由的最强大的组织形式之一,但只有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自治、政治科学普及到社会最底层的民族才适合这样的政府;墨西哥人也希望实行联邦制,便把美国的联邦宪法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过来,然而只抄走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将赋予宪法生命的精神也一并移植过来,因此各种不适,一直走不出从无政府状态到军事专制,再从军事专制到无政府状态的恶性循环。林奇的《玻利瓦尔传》指出,在玻利瓦尔看来,只有缔造拥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大型民族国家,才能克服美洲群雄并立的乱局。这本传记展示了玻利瓦尔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是越来越偏向于集权的,这也是形势所迫——他越来越忍受不了独立战争造成的无政府主义乱局。如果自由逐渐堕落成无法无天,如果民主逐渐滑向多数人的暴政,那么他宁可选择专制。
1819年,在安戈斯图拉,玻利瓦尔面对国会代表们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其遵照法国或北美的范例,不如从英国吸收经验——当然不是施行君主制,而是从等级制结构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出发,设立一个由民意代表选举的众议院和一个世袭的参议院,建立一个虽由选举产生但权力巨大并且集中的行政机关,再设立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并且再加入第四权——道德权力,以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和政治美德。约翰·林奇评价说,世袭参议院的设想,是要对绝对民主加以限制,其缺陷在于,这会使委内瑞拉的领主式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和延续;所谓“道德权力”,是一个拙劣的构想,但也表明了玻利瓦尔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良苦用心。到了1826年,玻利瓦尔在他起草的玻利维亚宪法中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总统实行终身制,并有权指定继承者,因为“共和国总统历来是如同处于宇宙中心的、给万物以生灵的太阳一样的人物”。这在美洲人当中招致了激烈的非议。他还希望将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国家结成联盟,采用他的宪法,这更是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希望破灭后,他面对的是老部下带头造反、苦苦维系的共同体分崩离析的危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约翰·林奇看来,若是没有玻利瓦尔,美洲的独立革命就会走向崩溃,考迪罗们会成为最终的统治者,唯有他具有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政治统一的韧性,他对国际形势的卓越判断力也是他领导的独立斗争能获得胜利的关键,而权力与荣耀的加身也使得“他的原则不再纯洁”,最终走向众叛亲离的凄惨境地。玻利瓦尔在为美洲解放事业奋战多年后,竟如此总结他的经验:“投身革命,犹如在大海犁田;在美洲,能做的只有移民海外……如果世界上有哪一个地方有可能重返原始的混沌,那将是末日降临的美洲。”
是美洲人配不上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吗?拉丁美洲从它的诞生开始就注定不可救药吗?独立以来两百多年的拉美历史证明,人民不应当被动地期待任何一个“解放者”,这种期待只会一次次地变成恐怖梦魇。民族获得解放,每一个人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解放,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某个“圣徒”,这仍然是一种前现代的观念,是未有启蒙的意识状态。“我们的美洲”,应当由具备现代政治理念的政治家和具备现代政治意识的人民共同缔造。主张英雄崇拜的苏格兰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有这样一句名言:“世界历史是一部无限的神圣的书,所有人都是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也都是这本书中的人物。”历史不单是像西蒙·玻利瓦尔这样的杰出之人创造的,也是所有人创造的。